会员登录
如果您志在餐饮,请联系我们,我们为您竭诚提供全套的餐饮咖啡解决方案。
如果您想在办公室喝到与高档咖啡馆一样品质的咖啡,请联系我们。我们为您量身定制最合适的办公室咖啡套餐。
010 - 8049 0710
021 - 6428 8941
北京:infobj@arabicaroasters.com
上海及其他地区:infosh@arabicaroasters.com
Outside 户外

详细介绍

《Outside》于1978年在美国创刊,发展到今天,已经是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户外杂志,每月读者超过200万(数据来源:MRI Market Solutions Division)。入选2005年全球杂志势力TOP100排行榜,是唯一一本进入前100名的户外类杂志。同时也是美国出版史上唯一一本连续三年获得杰出期刊大奖(National Magazine Awards for General Excellence)的杂志。
2006年10月,《Outside》来到中国,中文名为《户外》。《户外》将继续秉承《Outside》“倡导积极健康生活方式”的理念,为中国读者提供全球同步的户外现象、行为、事件的客观报道,并涉猎人文地理、科学探险等内容。在讲述精彩有趣的户外故事和户外人的同时,我们努力传递一种乐观向上的价值观——梦想、勇气、自我实现、热爱自然、追求自由……
视频: Outside《户外》杂志
视频: Outside《户外》杂志
户外的使命是通过获奖的体育、人、地方、冒险、发现、健康和健身、工具和服饰、趋势和活动来激发积极的生活方式,以激励世界的积极参与。
户外一直都在推动搜索创新的方式将人们连接到外面的世界。随着互联网有一个全探索层深度增加,这使得现在户外在线成为真正激动人心的地方。
Hola Argentina
时长1个月、行程逾1万公里、海拔上下7000米、几乎环绕整个阿根挺的一场探险,一部关于南美的冒险纪录片……感觉属于MINI探险队的疯狂。
整个一月,杨波和他的几位伙伴都晃荡在阿根廷的广阔荒原上。他们驾着MINI COUNTRYMAN,体验达喀尔拉力赛的狂野路段,沿着安第斯山脉一路往南,直到巴塔哥尼亚高原最南端的雪山和冰湖,途中以令人惊愕的速度登顶了海拔6962米的美洲大陆最高峰阿空加瓜。
这趟MINI冒险之旅对这个久经各种户外考验、各个身怀绝技的团队来说,是一个又一个壮阔奇观的接力,也是一个又一个小冒险的叠加。作为户外杂志主编,杨波说,这是他过的最疯狂的新年。
冒险从签证开始


至于中国的驾照能否在阿根廷开车?这也像一场小冒险。我们在各种可能的渠道发问,奇怪的是,似乎以前从来没有中国人在那边开过车,没有人能告诉我们答案。

开车像滑雪一样刺激

奇葩速度登顶“美洲巨人”

海拔6962米的阿空加瓜峰是南美洲,也是整个南半球的最高峰,位于阿根廷与智利交界的门多萨省的西北端,远远高出安第斯山脉范围内其他的山峰,所以还有一个“美洲巨人”的绰号。比起喜马拉雅山区的那些技术性雪山,阿空加瓜算是比较容易的山峰。但绝不能小视,因为其巨大的海拔高差以及漫长的进山路线对攀登者的体力要求可能要排在七大洲最高峰里的前列。对我们来说,由于还要赶去大陆最南端,所以几乎没有留出适应海拔的时间,高反、寒冷、大风着实考验了我们这支经验丰富的登山队伍。

从门多萨城出发到大本营就花了两天,坐了两段车,总共徒步漫长的10个小时。16日,6个人讨论攀登计划,结果一人一个主意,连周鹏李爽这对夫妻都是如此。而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4天之后将是连续三天糟糕天气,最后大家好不容易达成一致,在大本营休息一天,然后跳过一个营地快速上升,赶在19日冲顶。

Hola Argentina
时长1个月、行程逾1万公里、海拔上下7000米、几乎环绕整个阿根挺的一场探险,一部关于南美的冒险纪录片……感觉属于MINI探险队的疯狂。
整个一月,杨波和他的几位伙伴都晃荡在阿根廷的广阔荒原上。他们驾着MINI COUNTRYMAN,体验达喀尔拉力赛的狂野路段,沿着安第斯山脉一路往南,直到巴塔哥尼亚高原最南端的雪山和冰湖,途中以令人惊愕的速度登顶了海拔6962米的美洲大陆最高峰阿空加瓜。
这趟MINI冒险之旅对这个久经各种户外考验、各个身怀绝技的团队来说,是一个又一个壮阔奇观的接力,也是一个又一个小冒险的叠加。作为户外杂志主编,杨波说,这是他过的最疯狂的新年。
大咖团队:这样一趟疯狂的旅程,没有一个冠绝户外和影像界的团队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
苏荣钦(阿苏):摄像师里最厉害的登山者,登山者里最厉害的摄像师。
李爽:无论男女,导演里最厉害的登山者。
周鹏:自由攀登者,亚洲金冰镐奖获得者。与李爽是夫妇。
康华:BD品牌总监,登山“老前辈”,登过的雪山数不清。
杨波:户外杂志主编,曾经一天爬上7000米雪峰,然后滑雪下山。
Tim:美国退伍军人,攀登过珠穆朗玛峰、北美及非洲最高峰。执导的多部户外运动纪录片获得诸多电影奖项。
MINI Countryman:越野拉力明星,此前已经达喀尔三连冠。
故事由杨波来讲。
冒险从签证开始

出发前我觉得,有钱有MINI,走遍天下都不怕。没想到,冒险从签证就开始了。阿根廷政府对中国的签证政策格外严厉,比以麻烦出名的美国签证还要麻烦十倍。你得拿出一切可能的材料,让签证官相信你不会滞留在他们国家。
相比之下,美籍人士Tim,拿着他的国际驾照,买张机票就直飞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了。那才叫“一场想走就走的冒险”。

至于中国的驾照能否在阿根廷开车?这也像一场小冒险。我们在各种可能的渠道发问,奇怪的是,似乎以前从来没有中国人在那边开过车,没有人能告诉我们答案。

和搞签证相比,装备准备和身体锻炼反而很轻松,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疯狂的经历,所以没什么担心的。
在不透明和繁琐的签证政策几乎要消磨掉我对这个国家原有的全部好感之际,我们在1月2日踏上了阿根廷的土地,耀眼的阳光、清澈的蓝天让我顿时好感重生。
开车像滑雪一样刺激

和以前的各种探险活动不同,这次驾驶就是探险的一部分,MINI就是我们团队的一个伙伴。
一趟开下来,一向对摩托车更有兴趣的我成了汽车驾驶爱好者。转变最大的要数阿苏,这个本来不会开车的人上手之后欲罢不能,被我们无情拒绝还会绝望地大喊:“我要开车!”这一方面是由于阿根廷的路况,另一方面源于MINI带来的操控乐趣。

俗话说,“坐奔驰,驾宝马”,MINI作为宝马的一份子,自然继承了优异的操控基因,加上更轻巧的车身,优势更为明显。我是个疯狂的滑雪迷,一向喜欢追逐高速和刺激。在我看来,驾驶MINI和滑雪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好的雪板,高速切弯时能够深深切入雪面,快速流畅地完成转弯,MINI车也是如此,过弯时能够体会到四轮牢牢抓住地面,让驾驶者信心大增。我也喜欢越野摩托,MINI的强劲动力,让我找到驾驶越野摩托的感觉。这一路上大多数路面都是双向单车道,这让超车的危险性大大增加,但MINI的出色性能和异常便捷的操控,让超车变得像打赛车游戏一样乐趣十足。

我们所走过的一些地方同时也是达喀尔拉力赛的路段,未加铺装的乡村路,甚至更简陋,高速开过之时,烟尘在车后拉起一道白烟,在镜头里极为壮观。或者就是那种上下起伏、左右曲折的沙石路面,一度我和周鹏在这样的路面玩追逐游戏,在烂路上也跑80公里左右的时速,像极了滑雪追逐赛的场景。MINI在这样的路面上依然保持了极好的操控性,你全身贯注盯着路面,全凭下意识操纵,车就像是身体的自然延伸,这种人车一体的感觉好极了。

俗话说,“坐奔驰,驾宝马”,MINI作为宝马的一份子,自然继承了优异的操控基因,加上更轻巧的车身,优势更为明显。我是个疯狂的滑雪迷,一向喜欢追逐高速和刺激。在我看来,驾驶MINI和滑雪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好的雪板,高速切弯时能够深深切入雪面,快速流畅地完成转弯,MINI车也是如此,过弯时能够体会到四轮牢牢抓住地面,让驾驶者信心大增。我也喜欢越野摩托,MINI的强劲动力,让我找到驾驶越野摩托的感觉。这一路上大多数路面都是双向单车道,这让超车的危险性大大增加,但MINI的出色性能和异常便捷的操控,让超车变得像打赛车游戏一样乐趣十足。

我们所走过的一些地方同时也是达喀尔拉力赛的路段,未加铺装的乡村路,甚至更简陋,高速开过之时,烟尘在车后拉起一道白烟,在镜头里极为壮观。或者就是那种上下起伏、左右曲折的沙石路面,一度我和周鹏在这样的路面玩追逐游戏,在烂路上也跑80公里左右的时速,像极了滑雪追逐赛的场景。MINI在这样的路面上依然保持了极好的操控性,你全身贯注盯着路面,全凭下意识操纵,车就像是身体的自然延伸,这种人车一体的感觉好极了。
奇葩速度登顶“美洲巨人”

海拔6962米的阿空加瓜峰是南美洲,也是整个南半球的最高峰,位于阿根廷与智利交界的门多萨省的西北端,远远高出安第斯山脉范围内其他的山峰,所以还有一个“美洲巨人”的绰号。比起喜马拉雅山区的那些技术性雪山,阿空加瓜算是比较容易的山峰。但绝不能小视,因为其巨大的海拔高差以及漫长的进山路线对攀登者的体力要求可能要排在七大洲最高峰里的前列。对我们来说,由于还要赶去大陆最南端,所以几乎没有留出适应海拔的时间,高反、寒冷、大风着实考验了我们这支经验丰富的登山队伍。

从门多萨城出发到大本营就花了两天,坐了两段车,总共徒步漫长的10个小时。16日,6个人讨论攀登计划,结果一人一个主意,连周鹏李爽这对夫妻都是如此。而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4天之后将是连续三天糟糕天气,最后大家好不容易达成一致,在大本营休息一天,然后跳过一个营地快速上升,赶在19日冲顶。

大本营像个热闹的联合国小村,气氛轻松欢快,常有庆祝登顶的音乐Party,不像国内登山有时会有种悲壮的气氛。甚至还有爱好登山的画家在这里搭了一个画廊,展示他笔下各个角度各种面貌的阿空加瓜。
17日出发,离开大本营时每人发了三个黑色塑料袋,用来装大便,必须将自己的排泄物带下山。老实说,这是头一次使用,老大不习惯。可怜的康华,憋了好几天,都快便秘了。

一路向南狂奔到尽头

离开门多萨,我们开始了真正自由的行程,朝着大陆最南端的雪山冰湖前进,原则只有一个,就是能赶回布宜诺斯艾利斯搭上回国的航班。走到哪儿天黑,就在哪儿歇。自由的感觉是如此美妙,一路上,我们在车上听得最多的歌曲就是电影《被解放的姜戈》主题曲《自由》,兴之所至,心花怒放。

对于攀登者来说,巴塔哥尼亚高原上的陡峭雪山Fitz Roy、Cerro Torre是梦想之地,没有机会攀爬,但为了亲眼看一下也值得狂奔6000公里。我们基本沿着40号国家公路(Ruta Nacional 40)一直往南。这是阿根廷最长的公路,从与玻利维亚交界处的La Quiaca开始,向南延伸到巴塔哥尼亚最南端的Cabo Virgenes,全长4900公里,从大西洋海岸攀升至4905米高的安第斯山脊,沿路经过236座桥、18条大河、13片湖泊、20个自然保护区、27个山口。80年前始建至今,铺过路面的路段仍然不到一半,这恰恰是吸引公路冒险迷之处。

旅行者Vaquita曾经这样描述:“在Ruta 40上行驶,本身就是一种特别的体验。寂寥的公路上渺无人烟,每隔半小时迎面驶过一辆车,相互以手势打个招呼,沿途风景任凭吸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自由足够美妙,但也意味着责任。我们行经的大部分区域都是穷乡僻壤,英语毫无用武之地,手机和网络信号又糟烂之极,搞得每天的吃住行都像一场小冒险。经常半夜闯入一个陌生小镇,挨家找旅馆,和完全语言不通的老板手舞足蹈比划半天,才得以入住。久而久之,阿苏练出了特殊本领,能够在不说一句话的情况下单靠比划,就和店老板完成复杂的沟通——大床间、双人间、三人间,还有讨价还价。李爽则学会了各种吃喝的西班牙语说法,常能博得饭馆老板点赞。

八天狂奔六七千公里,其中还不乏崎岖山路,还是颇有压力的,基本是开车的累死,不开车的闲死。但跟几次差点弹尽油绝的惊险相比,起早贪黑赶路都不算问题。一路油站分布稀疏,甚至两三百公里不见人烟,更别说油站了。好几次油表显示只能跑十来公里了,几乎绝望之际,突然出现一个救命的加油站,简直就是提前算好你刚好能跑到这里。还有一次,油表显示还能跑一百多公里,我们大着胆子试图东西横穿荒漠,一路人烟全无,心里犯嘀咕,好不容易碰到对面来车,拦住司机一阵比划,才知道这条荒漠土路得开出去350公里才有油站。赶紧乖乖掉头另寻他路。回过神来禁不住庆幸,幸好遇见了这辆车,否则黑灯瞎火困在茫茫荒漠中,呼天不应,叫地不灵,那就是大冒险了。

当Fitz Roy近在眼前的时候,我们只有呆立赞叹她的美貌。之后,我们深夜赶到了Ruta 40的尽头Rio Gallegos。寻着一家24小时快餐店,强睁着惺忪睡眼开吃。李爽有点带着哭腔问道,“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赶路啊?”还没等我们回答,她自己就明白过来了,“我想了,就是再给我们一个月,我们还是会这么赶,因为阿根廷可以转的地方太多了,我们又太贪心了。”

谁都没有预料到,在阿根廷的最后一天,竟然算得上这一整个月里最大的冒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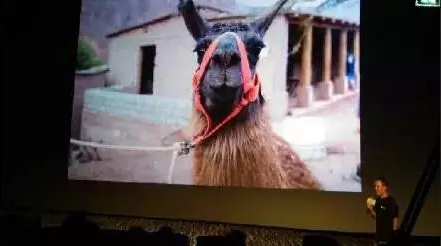
5月,我们拿出一个版本送到班夫户外电影节。北京三里屯美嘉影城440人的放映厅座无虚席,晚到的观众甚至坐到了台阶上。电影放映和后面的分享会,我们让大家爆笑了很多回。后来在上海喜马拉雅大观舞台放映时,场地还要更大,但影院设备出了故障,影响了放映效果,很可惜。对于影评,我们听到的都是好话——但我猜测大家也不敢当面给我们提不好的,呵呵。

这部30分钟的《Hola,Agentina》凝结了我们一路感受到的壮美、热情、乐趣,以及在困境之下的坚持和理性。这是属于我们的探险,也是我们想带着观众一起去经历的疯狂旅程。

随后的一天,一路顺利抵达海拔6000米的营地。但是在夜里,赶时间造成的各种不适感终于爆发,连经验最丰富的周鹏都很久没有过这么难受的感觉了。凌晨4点40,我们摸黑出发冲顶。我穿得几乎比任何一次登山穿的衣服都要多,还是止不住发抖。早上不想吃东西,结果出发没多久就饿得不行,加上透骨的寒冷,我都快要放弃了。康华更惨,戴着护脸眼镜起雾,摘下护脸结果鼻子冻伤,差点没能登顶。日出之后,气温稍微回升,这才好过一些。我们最终在上午11点15分作为当天头一拨登顶。下撤飞快,一鼓作气,下午5点就回到了大本营。
经过漫长的一天回程,我们深夜抵达门多萨,顾不得放行李,直接冲进当地有名的Patio自助烧烤店大快朵颐。
从门多萨城出发到返回,我们前后只用七天,正常队伍通常计划十六天左右。当地向导和背夫们直呼强悍。事实上,我们要是再疯狂一点,甚至有可能五天完成。
一路向南狂奔到尽头

离开门多萨,我们开始了真正自由的行程,朝着大陆最南端的雪山冰湖前进,原则只有一个,就是能赶回布宜诺斯艾利斯搭上回国的航班。走到哪儿天黑,就在哪儿歇。自由的感觉是如此美妙,一路上,我们在车上听得最多的歌曲就是电影《被解放的姜戈》主题曲《自由》,兴之所至,心花怒放。

对于攀登者来说,巴塔哥尼亚高原上的陡峭雪山Fitz Roy、Cerro Torre是梦想之地,没有机会攀爬,但为了亲眼看一下也值得狂奔6000公里。我们基本沿着40号国家公路(Ruta Nacional 40)一直往南。这是阿根廷最长的公路,从与玻利维亚交界处的La Quiaca开始,向南延伸到巴塔哥尼亚最南端的Cabo Virgenes,全长4900公里,从大西洋海岸攀升至4905米高的安第斯山脊,沿路经过236座桥、18条大河、13片湖泊、20个自然保护区、27个山口。80年前始建至今,铺过路面的路段仍然不到一半,这恰恰是吸引公路冒险迷之处。

旅行者Vaquita曾经这样描述:“在Ruta 40上行驶,本身就是一种特别的体验。寂寥的公路上渺无人烟,每隔半小时迎面驶过一辆车,相互以手势打个招呼,沿途风景任凭吸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自由足够美妙,但也意味着责任。我们行经的大部分区域都是穷乡僻壤,英语毫无用武之地,手机和网络信号又糟烂之极,搞得每天的吃住行都像一场小冒险。经常半夜闯入一个陌生小镇,挨家找旅馆,和完全语言不通的老板手舞足蹈比划半天,才得以入住。久而久之,阿苏练出了特殊本领,能够在不说一句话的情况下单靠比划,就和店老板完成复杂的沟通——大床间、双人间、三人间,还有讨价还价。李爽则学会了各种吃喝的西班牙语说法,常能博得饭馆老板点赞。

八天狂奔六七千公里,其中还不乏崎岖山路,还是颇有压力的,基本是开车的累死,不开车的闲死。但跟几次差点弹尽油绝的惊险相比,起早贪黑赶路都不算问题。一路油站分布稀疏,甚至两三百公里不见人烟,更别说油站了。好几次油表显示只能跑十来公里了,几乎绝望之际,突然出现一个救命的加油站,简直就是提前算好你刚好能跑到这里。还有一次,油表显示还能跑一百多公里,我们大着胆子试图东西横穿荒漠,一路人烟全无,心里犯嘀咕,好不容易碰到对面来车,拦住司机一阵比划,才知道这条荒漠土路得开出去350公里才有油站。赶紧乖乖掉头另寻他路。回过神来禁不住庆幸,幸好遇见了这辆车,否则黑灯瞎火困在茫茫荒漠中,呼天不应,叫地不灵,那就是大冒险了。

当Fitz Roy近在眼前的时候,我们只有呆立赞叹她的美貌。之后,我们深夜赶到了Ruta 40的尽头Rio Gallegos。寻着一家24小时快餐店,强睁着惺忪睡眼开吃。李爽有点带着哭腔问道,“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赶路啊?”还没等我们回答,她自己就明白过来了,“我想了,就是再给我们一个月,我们还是会这么赶,因为阿根廷可以转的地方太多了,我们又太贪心了。”
出乎意料的终极惊险

谁都没有预料到,在阿根廷的最后一天,竟然算得上这一整个月里最大的冒险。

1月29日中午,沿着大西洋海岸狂奔2500公里之后,我们赶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机场,似乎还早到了几个钟头。我和李爽驾着MINI去到市区还车,余下几人则收拾行李准备登机事宜。没成想,手机导航失灵,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里的道路又太复杂,我们迷路了。好不容易找到地图上标注的宝马公司驻地,却发现是个大工地,四处问路无果。幸好电话联系上了宝马的人,费尽周折总算接上了头。还完车赶紧叫上出租车朝机场狂奔,天哪,布宜诺斯艾利斯也像北京一样堵车。祸不单行,半途李爽一声大叫,“完了,我护照落在MINI车上了,赶紧掉头。”司机边开边找出口,我心里苦笑,这下铁定赶不上航班了。还没找到出口,李爽在她的背包夹层里翻到了护照。这一惊一乍,能把人活活吓死。
出租车一路冲到机场,几位同伴已经等到绝望,没想到我们能在最后一分钟赶到。踏上登机口,李爽感叹,“我觉得今天是这一个月里最冒险的一天。”我也同意。
微电影大工程
老实说,在这样的行程当中去制作一部微电影,本身就是一个疯狂的念头。除了折腾签证之外,我们在行前花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讨论拍摄计划和分工。但真正进入拍摄仍然困难重重。
拍摄由阿苏、Tim和李爽分担。前半程,我们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团队一同参加MINI主办的达喀尔体验活动,总感觉不好意思耽误大伙儿的行程,每天都对其他国家的队员们赔笑。攀登阿空加瓜的时候,忍着剧烈的高反,背着摄像器材,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低温,顶着呼啸的大风,坚持开机拍摄。这活,一般人真干不下来。
李爽、阿苏和Tim每天要拍摄海量素材,视频、音频、图片,每天大概都有一两百个G。李爽负责最终的制作成片,回来之后光是把整个素材过一遍,都快把她看吐了。为了最完美的呈现效果,片子一再修改,直到8月初才最终定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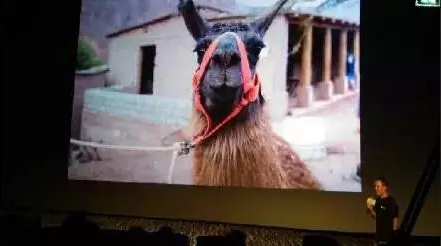
5月,我们拿出一个版本送到班夫户外电影节。北京三里屯美嘉影城440人的放映厅座无虚席,晚到的观众甚至坐到了台阶上。电影放映和后面的分享会,我们让大家爆笑了很多回。后来在上海喜马拉雅大观舞台放映时,场地还要更大,但影院设备出了故障,影响了放映效果,很可惜。对于影评,我们听到的都是好话——但我猜测大家也不敢当面给我们提不好的,呵呵。

这部30分钟的《Hola,Agentina》凝结了我们一路感受到的壮美、热情、乐趣,以及在困境之下的坚持和理性。这是属于我们的探险,也是我们想带着观众一起去经历的疯狂旅程。
